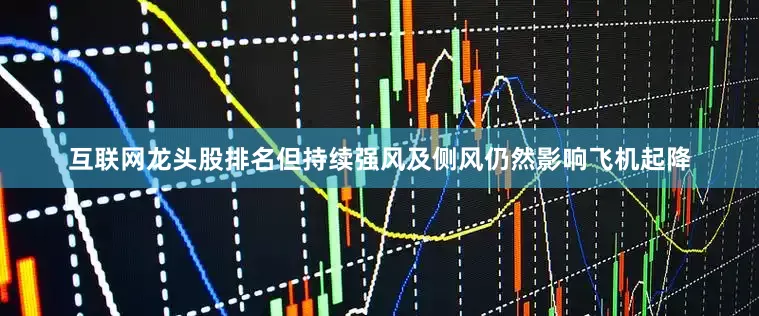■ 本报记者 林晓晖 通讯员 盛灿灿
蒋风已经一百岁了。
安静的病房里,时间的流逝似乎都停止了。老人佝偻着背,眼睛凑得极近,几乎要贴上摊开的书页。一只陪伴他许久的长柄放大镜,此刻也稍显“力不从心”。“它都帮不上大忙咯。”他抬起头,乐呵呵地说。
这里俨然是一间“书房”。床沿、床头柜、窗台,都成了临时的书架,厚重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、色彩跳跃的童话书和绘本叠放在一起。
相比于身体的迟缓,说起话来,蒋风依旧中气十足,条理清晰,思维活跃。得知记者要来,他换上熨帖的衬衣,领口挺括,透着读书人的风骨。这份执着,也贯穿了他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事业。
蒋风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开创者,在浙江师范大学首开全国高校儿童文学硕士培养先河,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……曾经长期“荒芜”的中国儿童文学,在他的耕耘下有了坚实的学术根基。
横跨一个世纪,太多事物在变迁,可蒋风身上有很多始终不变的东西——他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勤恳钻研,聊起儿童文学,有说不完的话。过几天,一年一度的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又要开办,他坚持视频连线,一字一字准备讲稿,见到那些热爱童心世界的面孔,他感到兴奋和期待。
展开剩余88%一个人的“光荣荆棘路”
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,蒋风也几乎没有休息。
他仍在修订自己的研究著作。时代在变,理论也需要更新。前几年,91岁高龄的蒋风申报了《世界儿童文学事典》(修订本)的课题,这是儿童文学研究第一次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。
300多万字的篇幅,历经五年多的编撰、修订与校对,它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,也是资料最齐全、内容最丰富的儿童文学研究大型工具书。
如此高龄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,超乎常人想象。
“这本书是我的孩子,我希望它更加完美。补充内容数量很多,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课题。”蒋风顿了顿,“我不是想逞英雄,只是,我不做,可能就没人做了。”
他有种“责无旁贷”的使命感。这份使命,深植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艰难的起点,支撑着他近乎执拗的坚持。
上个世纪50年代,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。在社会普遍认知里,儿童文学不过是“小猫小狗叫”的“小儿科”。
1978年10月,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首届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上,专家们疾呼:必须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匮乏的现状,高校必须恢复儿童文学课并招收研究生!参会的蒋风心潮澎湃。
参会归来,蒋风立刻向浙江师院领导力陈开设儿童文学课的必要性。当时,一无人力、二无资金、三无设备,他独自扛起了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的重担。浙江师院由此成为新时期全国首个重启该课程的高校。
刚起步的蒋风,是彻头彻尾的“光杆司令”。
在全国“招兵买马”时,他看中了云南教育学院的老师韦苇,欣赏其文笔和外语能力。为了促成调动,蒋风不辞辛劳,四处奔走,向省教育厅说明情况。经过两年的努力,韦苇终于调入。
“把我从西南边陲招募到浙江,在当时,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。”如今想起,韦苇仍佩服蒋风对儿童文学的热忱和决心。
“儿童文学不是‘小儿科’,而是‘种太阳’的事业!它影响着孩子的心灵,塑造着人类的未来。”蒋风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人。
1982年,蒋风专著《儿童文学概论》出版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系统性的儿童文学专著。
“孩子是人类的未来,儿童文学是他们最早的教科书。”
蒋风认为,耙梳和构建起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,是儿童文学走向真正独立学科的必由之路。
这条路,正如安徒生所形容,充满“光荣与荆棘”。光荣,在于其塑造未来的深远意义;荆棘,则因为拓荒一个从零开始的学科,注定是一场漫长、艰辛的跋涉。
1995年,蒋风已经离休,再次以一人之力创办《中国儿童文学信息报》。这份季刊,每期印刷3500份,无偿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华文儿童文学研究者。
从组稿、选稿、设计版面、校对、送印,到一份份仔细装入信封,再跑邮局寄出,他事必躬亲。唯一的经费来源是他的离休金,仅有的帮手是他的妻子卢德芳和几位热心的研究生。
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,严重透支了蒋风的健康。
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管狭窄,曾经步履矫健的老小伙,如今去哪儿都离不开助行车。后来,他安了心脏起搏器,带状疱疹又损害了他的视力,眼睛几乎看不见了。“他说白天工作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疼痛的,一到晚上其实非常难受。”妻子卢德芳说。
蒋风家里的地板上,有两道明显的印痕,在他长期伏案的书桌下,还有两个深深的脚窝。卢德芳告诉我,这是因为蒋风工作的时间和路线非常固定,几乎“不挪窝”。
印痕的起点是蒋风的卧室,穿过客厅,一直延伸进书房。这是助行车的轮子天长日久地在地板上留下的,也是蒋风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行进的轨迹。
一片儿童文学的“森林”
给学生们的作品写序言,是蒋风最开心的事。
看着一个个学生成长,出成果,儿童文学事业从一个人的坚守,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。蒋风相信,只有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,儿童文学带来的那些细微却深远的改变,才能真正发生。
许多年前,一位金华的小学老师找到蒋风。她热爱儿童文学创作,不追求正式的硕士学位,只想学点实在的理论,创作上能得到指点就满足了。
这番话像颗种子,落在蒋风心里,让他坚定了要办一所不一样“大学”的念头:不看国籍、年龄、职业,只要真心喜欢儿童文学,都能来学。
于是,1994年,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在金华成立,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,举办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。
30多年来,这所“不收费的大学”招收了1500多名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。学生里,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,也有70多岁的长者,更多的是中青年。他们是作家、编辑、记者,是幼儿园、中小学或大学老师,来自各行各业。
知名童话作家汤汤,成为作家前,是武义县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。2003年,汤汤参加了在武义的讲习班。“就因为听了那几天的课,我对儿童文学一下子着了迷。”汤汤回忆说,“心里那股劲儿压都压不住,就想着以后课余时间写童话,念给班上的孩子们听。”这成了她童话路的起点。
更广泛的人群被吸引进儿童文学的天地。蒋风播撒的种子,已悄然长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。
这里,不仅走出了汤汤这样的新生代作家,2022年,讲习班的6位学员同时加入中国作协,还有大批的乡村教师把儿童文学理论运用到了课堂教学。这片森林的绿意,更延伸至国门之外。
一次偶然,蒋风在国外刊物上看到日本儿童文学著名学者鸟越信的名字,主动去信联系。鸟越信的回信,开启了一段深厚的学术友谊。
后来蒋风赴日参加国际会议,在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做研究,乃至归国后筹建中国首个国际儿童文学馆,都得到鸟越信倾力相助。蒋风也邀请鸟越信前来讲学。“当时经费困难,开不出讲课费。”蒋风说起,仍感念学术情谊的纯粹,“鸟越信先生得知后,主动提出分文不取。”
2011年,蒋风凭借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,荣获第13届国际格林奖,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。
这是儿童文学领域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,评委会在颁奖词中郑重评价:“他以毕生精力搭建起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,其创办国际儿童文学馆、推动学科建设等创新举措,填补了该学科在中国的多项空白,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真正跻身世界前列。”
他是公认的大学者,有大智慧。可蒋风心里,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。
蒋风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。慕名请教的人络绎不绝,但他总能及时回复。他习惯手写信,给予详尽的解答。
一次,一位“徒孙”向他请教其早年著作中的一个观点,很快收到了蒋风的亲笔回信。信中,溯源、引例,严谨细致。言辞间,完全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后辈视作平等的交流者。
“当年写的文字,科学性与系统性都是很不够的,仅仅是探索而已。”他因为没能完全帮上忙还有些内疚,“我因年老眼花,未能帮你作更科学的考证,实感抱歉,请原谅。”他恳切地写道。
一颗不泯的童心
“花红了,草绿了/莺儿站在树梢头,唱着迎春的曲调/啊!原来春天来了/小朋友!/切莫把春光辜负了!”
1936年,少年蒋风在郑振铎主编的《儿童世界》上发表了第一首儿童诗《春天来了》。80多年后,一位学生从旧书堆里找出这首诗,复印给他。百岁老人摩挲着纸页,轻轻念出声。
儿童文学深深滋养了蒋风的性格。他天真、浪漫,期颐之年,岁月也没有销蚀他骨子里散发的这股童真。
今年春节,家人给他下载了“豆包”。老人兴致勃勃,对着手机接连抛出问题:“你了解蒋风吗?”“蒋风今年100多岁了,还能做些什么?”“蒋风有什么不足之处?”他想看看,这个智能体能否映照出他对自己人生的思考。
幼年时,不识字的母亲常常吟诵朗朗上口的古诗,小学老师每周安排故事课,蒋风仍然记着那些温柔的诵读声和发亮的眼睛。
让蒋风下决心走上儿童文学道路的,是1947年《申报》上的一则新闻。3个孩子受荒诞儿童读物的迷惑,去峨眉山“修仙”,最后跳崖身亡。这条剪报消息,他至今保存着。
“这些荒诞的书对孩子的伤害多大啊!”蒋风十分感慨,那个年代,真正的少儿读物是奇缺的。
那么,真正的儿童文学该是什么模样?
“应如溪水般自然流淌,纯净无碍。”蒋风常常自比为“花瓣上的雨露”,一颗小小的水珠,晶莹、纯洁,给世界增添一丝美好。
对儿童文学创作,他总结出三个朴素的准则:有益、有趣、有味。“孩子们没兴趣的书,看不下去;有害的书,会伤人;唯有那些蕴含生命力的文字,才能滋养心灵。”
谈到儿童诗的语言,蒋风把手捏成一个拳头,在我面前用力扬了扬:“要像一颗小炸弹,蕴藏爆发力和感染力;更要像一颗种子,孕育着开花结果的生命!”
不分年龄,没有国界,好的儿童文学能打动所有人。它能擦亮人们感知世界的眼睛,唤醒人们对身边人、一草一木乃至整个世界的温柔与爱意。
蒋风笃信这种力量。这些年,他发起了“私人藏书公益化”的阅读活动。他将自己半个多世纪积累的1万多册儿童读物、珍贵研究资料,以及与国内外著名作家的往来信件,悉数捐赠。
像孩子一样,蒋风有着做不完的梦。“这些梦想几乎都与儿童文学有关。”他的皱纹刻满额头,眼神却清澈如初。
人会老去,但一颗浸润在儿童文学里的心——永远年轻。
发布于:北京市配资平台排行榜第一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